尼采:道德是如何绑架个人的?原创 读书广记 2019-06-19 15:56:00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开头讲述了精神的三种变形:最初精神是一只负重的骆驼,它在“你应当”的号令下,于沙漠中游荡;直到某个时候,它才产生夺取自由的念头,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于是它摇身一变,成了一头狮子,怒吼着“我意愿”;最后,精神又从狮子变成了新生的小孩,形成一个开端、一种原初的运动。
《三种变形》写得十分晦涩,让许多读者感觉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其实,尼采这是在讲述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最初的时候,道德就像那只负重的骆驼,服从于“你应当”的指导;后来,他有了打破传统习俗的勇气,变成强而有力的狮子,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正因为它能够做自己,所以旧道德才被埋葬,而新道德就如孩子一样,茁壮成长。尼采认为那些占据德性讲坛的道德家已经没落了,“他们的时代已经完了”,因为他们跟自己的信徒都在昏昏欲睡中......

尼采(1844-1900)
道德感是否属于天赋?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有三种先天性的事物,他们是理性、本能和道德律。道德律根源于良知,是与生俱来的。康德在柏拉图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律令”,认为它不受经验制约,能够普遍适用,向人们发出一个无条件的、绝对的命令——即“你应当”!
然而,挥舞着道德的大棒,对人们高叫“你应当”,其根本目的并不是希望别人高尚,而是想让他们服从于自己。在传统道德的各种“你应当”的压迫下,人们就像负重的骆驼一样,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旧道德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威、一种命令,因此尼采在《朝霞》中说:
“人们屈服于道德,正如屈服于一位君王,或因奴性,或因虚荣,或因自私,或因退让,或竟是热昏,无思想,绝望,本身并无道德可言。”
他认为康德的“道德律令”只是迎合了德国人的国民性,他们很少愿意成就一番大事,却总是能服从就服从。“人不能没有某种他可以无条件服从的东西”——德国人如是说。早在康德之前,路德就宣布说必定有一种人对之可以信任的绝对存在,而那便是上帝。“与康德相比,路德更粗糙和更大众化,他要人们无条件服从一个人格,而不是一个概念。”
尼采否认道德是先天的、需要绝对服从,他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指出道德感来自于传统和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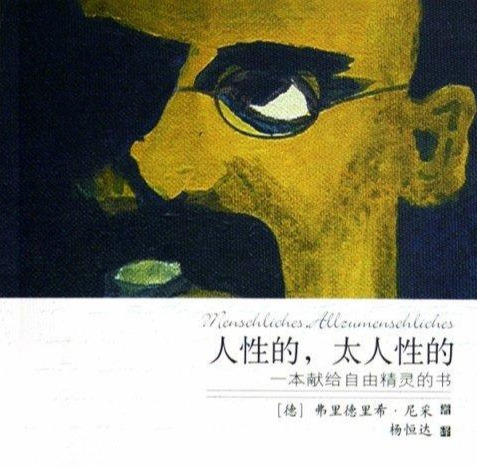
《人性的,太人性的·关于道德感的历史》
旧道德意味着服从于传统习俗狄德罗曾通过试验证明,天生盲人的道德观念与我们不同,他们对盗窃更为反感——因为人家很容易就能拿走他们的东西,却不被发觉。相反,他们对“非礼勿看”反而无动于衷。狄德罗说:
“一个比我们多有一种官能的生物会觉得我们的道德多么不完善,不用说更坏了!”
这个天生盲人的试验说明,道德感与经验存在着联系,它绝不是先验的。其次,道德感也不是永久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官能之发展、认识之进步而改变。
我们并非一生下来就具备道德感,而是不断地接受父母、老师的教育,受到书籍、网络的影响——是社会把道德观念灌输给了我们。人并不是基于求知才去认识道德,并建立道德体系;相反,他们是从已接受过来的道德观念出发,基于对这些道德的热爱,然而再去说明它们的合理性、为它们辩护。孔丘并不像研究自然界那样去研究道德,先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再去探究未知的事物。他生长在礼乐之风浓重的鲁国,从小耳濡目染,很早就认定服从于礼乐制度便是符合道德,后来才去提倡“克己复礼”,至于为什么要“复礼”?他很少讨论,因为这在他看来是不说自明的;柏拉图所说的“苏格拉底美德”也同样根源于习俗之中,他们的道德观念乃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这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道德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个体对传统观念和习俗的服从,如果不服从群体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违背大家所认可的观念,那就是离经叛道!因此,尼采说:
“讲道德、合乎道德、合乎伦理的意思是服从自古以来建立的法则或传统。人们是勉强还是欣然服从于它,这是无所谓的,只要人们服从于它就够了。”
这种道德所追求的并不是真理,也不是进步,而是服从。“善”并非正确,“恶”也无关谬误,利己不一定坏,利他也未必好,关键在于是否服从于传统的习俗与观念、是否服从于当权者或者主流的意识。如果传统与习俗很古老,那么道德就会让人感到敬畏,变成绝对权威,获得绝对命令的“道德律”。尼采说得好——
“他(康德)信仰道德,不是因为自然和历史证明道德的合理性,而是因为他决心置自然和历史的一再反驳于度外。”
道德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自然界哪有道德可言?原始人怎么会有道德感?为了避免道德的权威遭受这种现实的怀疑和攻击,康德才给“道德王国”安置了一个逻辑的“彼岸”,一个不可证明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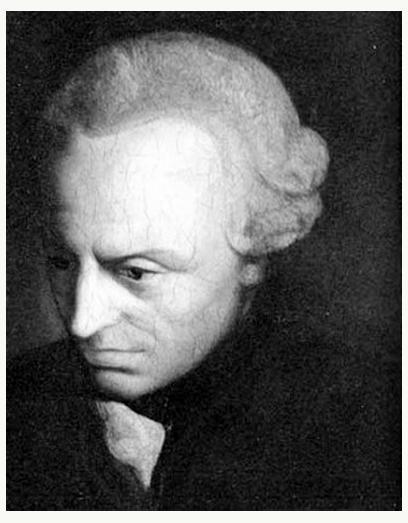
黑格尔、叔本华和尼采都从不同角度批判康德的道德学说
道德是如何绑架个人的?道德不需要证明,它就是权威,敢怀疑道德的人,就会被视为败类。所以何心隐和李贽都遭到了迫害,他们胆敢说什么“士贵为己,务自适”,这不是明摆着要否定传统习俗观念,搞自己的那一套么?可是这又算什么大罪呢?他们不过是追求更多的占有自己罢了,然而素以“仁恕”著称的道德,这时候却不那么宽容了!因为
“在道德面前,正如在任何权威面前,人是不许思考的,更不许议论:他在这里所能做的只有服从!”
卫道士们用各种恐吓手段来使批评之声不敢加诸道德,他们狭隘得容不下任何沉默。人们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触犯“道德的底线”的帽子,然而“道德底线”却不像“法律底线”一样清晰,它全由卫道士来裁定——道德就这样变成了杀人无形的利剑,到处都在制造恐惧。
此外,他们还有一种“勾魂艺术”,“为了说服别人,他们说起话来是多么道貌岸然,最后甚至自称起‘正人君子’来了。”他们挥舞着“你应当”的大棒,党同伐异,攻击私敌,抓辫子、扒老底、算旧账,这些把戏,东林党已经示范给我们看过了——当然,要是没有厂卫制度的配合,他们做起来又怎么能如此游刃有余呢?
道德是准绳、是规范,同时也是麻绳、是枷锁,全看人怎么使用而已。卫道士们最擅长利用道德这把屠刀,借助传统的习俗和公共的力量来打击自己的敌人,我们当心点罢——
“那班道德家不爱知识,只爱制造痛苦......其残酷的、可怜的快乐便是注意旁人的指头,悄悄在手指接触的地方藏一根针,使其刚好扎上。”
千万要谨言慎行呵!千万要当心卫道士的眼睛!

东林党人以道德名义排挤异己
旧道德的虚伪性虚伪仿佛是道德的影子,怎么也甩不掉。道德被鼓吹得更加完美无缺,虚伪的阴影也就愈发深刻。叔本华说:“道德,鼓吹易,证明难。”
卫道士们赞美道德,说它的目的在于人类的保存和进步。可是“保存人类的什么?往哪个方向进步?”是保存三跪九叩的习俗呢?抑或往“绝对服从”的沙漠中心更进一步呢?这些问题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从而显得目的的空洞。
道德蔑视一切没有同情的人,说“道德行动即出于同情别人而做出的行动”,这乃是一种虚伪。
当我们把别人的不幸遭遇设想为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才会产生同情心理。同情一个人就意味着在内心中觉得他的人格或境遇不如我,要依赖于我,有待于我的施舍。当我们给予他帮助之后,如果他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服从于我们的道德,不去帮助其他人而先求自保,我们又会嘟囔着“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了——原来我们帮助他,只是为了暴君式地对其进行强制改造,使他变得像我们自己而已。
要从“你应当”变成“我意愿”谁是最有道德的人?自然是那些遵守清规戒律、舍己为人的志士了,也就说——“最道德的人就是为习俗做出最大牺牲的人。”所谓的“最大牺牲”,就是不顾一切地服从于“道德律令”,这些人确实拥有着高尚的品格。
宋明两朝,愚民无知,汉奸倍出,然而也有少数士大夫肯舍生取义、以身殉国,这是理学深入知识阶层内心的缘故。不过也有不少的“你应当”压迫了许多人。例如赵光义说范质“但欠世宗一死”,朱元璋嘲笑危素不能像文天祥一样死节。弄到最后,连崇祯帝也被“责以大义”,不能南逃,只得以身死社稷了。

好好的“仁义道德”,怎么就因“你应当”而变成了“吃人”的工具呢?《乌合之众》说:“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而不摧毁传统,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或许,我们应该改变了罢!要怎么改呢?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喜欢折中,如果你把主张把房顶拆掉,他们就不愿意打开门窗。他们“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倘若不对旧道德进行彻底地破坏,新道德就不能新生。最后,新道德也就像看风水的罗盘、过烟瘾的鸦片、凑热闹的爆竹一样,迎合了愚民的传统。
尼采教导说:
“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切皆为习俗,谁想超越习俗,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成为立法者、巫医和某种半神之人:这也就是说,他必须自己动手创造习俗。”
不要再像奴子一样屈服于“你应当”了,而要像狮子一样考虑“我意愿”。尼采教导德国人,要想干一番事,总得先使自己超于旧道德之上。旧道德无关真理,只讲权威,新道德却要把它置于真理之下,重新审视:
“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思想上偏离道德,都不应再受到羞辱;必须对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进行大量新的实验;世界必须从愧疚和忏悔之心的阴影下解放出来:每一个正直、追求真理的人都应该认可和帮助实现这些广泛的目标。”
当然了,要变异一个民族的习俗又谈何容易?尼采自己也说“也许时机还未成熟”,不过他在《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中却坚定地对我们说:“不想沦为芸芸众生的人只需做一件事,便是对自己不再懒散,应听从良心的呼唤——‘成为你自己!’”
收藏
举报







 窥视卡
窥视卡 雷达卡
雷达卡
_conew1.jpg)


 提升卡
提升卡 置顶卡
置顶卡 沉默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变色卡 千斤顶
千斤顶 显身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