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阿来:批评家把姿态放低了,反而可能收获更多
原创 阿来 傅小平 文学报
伴随第七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揭晓的,是我们邀请了八位获奖者从各自文学观念出发,一起来探讨当下文艺评论环境里,如何“朝向‘真’的批评语境奋力前行”。
这些获奖者或是评论家身份,或是作家身份,或是横跨两者兼具一身,他们无一例外都尊重且期待着文学批评展现应有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贴近文本内部联结写作者的心灵,并将其拖入到当代历史的核心问题中去评价。
今天带来的是来自作家阿来的访谈。他认为,真正介入批评,首先就得贴着文本。同时,文学需要一种新意——“我们文学,也和艺术要处理新的材料一样,要处理一些过去文学没有处理过的新的东西,以及没有面对过的新的情感变化。”
文 / 阿来(受访) VS 傅小平(采访)
真正介入批评,首先就得贴着文本。如果是在预设的理论框架里分析作品,还是会隔。怎样才不隔呢,做好两个“贴”,一是贴语言,二是贴对象。
壹
批评家做批评,我觉得首先要跟批评对象之间有联结。
傅小平:《文学创作要“上天入地”》这篇文章,虽说是长篇演讲,但我是一开始就把它当批评文章来读的。当然联系到你作家的身份,我们可以称它为作家批评,融汇其间的那种文学性的表达,在批评家的文章里是不怎么见到的;要从批评视角上看,它又是一种带有综合性的广角批评,虽然主旨有关文学创作,但里面融入社会学、人类学的观察视角,显然让文章更有开阔气象。相比而言,我们读到的大多批评文章是为批评而批评,在一个比较狭窄的专业领域里打转。你强调作家创作要“上天入地”,我也关心批评家怎样能有这般的襟怀和气度?
阿来:批评家做批评吧,我觉得首先要跟批评对象之间有联结。钱穆先生说过一句话,对历史,尤其是本国的历史,要有一种温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这放在文学批评上,是一个道理。但我读很多批评文章,总觉得有点隔,有些生硬,那就是说有些基本的东西,批评家们还没做好。你说他们没做好,他们就会反过来说你不懂。其实他们把作家们看低了,那些道理,那些标准至少我都知道,我自己写文章,也会采用那些方法。我要深入自然,我总得了解一点植物学的知识,自然界的知识吧;我要了解地理,我总得学点地质方面的知识。我们要理解生活,就会用到各种各样的理论工具,经济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等等,我们都会用到。我们也不能不知道,要是完全不掌握这些工具,不明白这些介入的方法,一个事物就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看不见,甚至是一颗草、一棵树,我们都不认识。当然我们看见的也不一定都对,但我们要理性地去体验对象。
傅小平:掌握理论方法是理解生活、写好文章的必要条件,但肯定不是全部。刚我还想说,从批评方法上看,你的文章可以说是一种在场的批评,因为你是真正到了脱贫攻坚现场,而且用你自己的话说,是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客观地打量,深入地体察,这才带出来那么多鲜活的经验,并生发出深度的思考。你刚从凉山地区回来,这次走访也和这篇文章关注的扶贫攻坚主题有关系吗?
阿来:当然是有关系的,我们有些作家下去走访,我自己也去。我觉得这么大一件事情,我应该关注,倒不是说我下去后回来,马上要写什么,这不是我的习惯。如果我下去走访,只是为了写这么一个主题,其实也是划不来的。这里下面的市县、地方领导也可能了解我,有些作家下去,他们可能期望马上能看到什么成果,但对我没这个要求。那么,凉山地区有十几个县,这次去的这个县,是我以前没去过的。那个县委书记,三年前在另外一个县当县长,他现在到这个县任职了,他就说,哎哟,你别的县都看了,也得到我这里来看看。我就去了,也算是又填了一个空白。其实,像这样的走访,我大概走了有三年吧。讲扶贫攻坚这个事以前我就开始走了,当然我不是奔这个事去的,我是对相关写作感兴趣。
傅小平:深入现场后,扑面而来的新鲜感受会让我们不时做调整,并且还有可能改变我们“奔什么事去”的初衷。这次走访,想必你又有一些新的感触。
阿来:确实有一些,因为现实在不断发生变化,不断给你新的刺激。当然,从我个人来讲,很多新的变化,我也可以想象到。但无论生活也好,历史也好,社会也好,人性也好,我还是更关注那些恒常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像浪花一样附在表面上的东西。我们关注现实,都更容易看到起伏的浪花,而不是后面稳定的那些东西。社会要发展,要进步,新的东西或快或慢都会到来,但从文化,从人本角度来讲,我觉得更应该多关注那些历史规律性的东西。我虽然关注了,有些时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明白很多,但我更想搞明白这背后的东西,这是真的。
傅小平:你说的“这背后的东西”,我想很多人都能模模糊糊感觉到,而对于它到底指什么,又为何是这样,他们即便知其然,也很难说就知其所以然。
阿来:黑格尔讲的历史意志,我们也讲,但这个历史意志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文化里的显现或者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也不是一直往前,在社会发展当中,有时还会有怪异的动摇。从这个角度,我其实是有些悲观的。但我还是更关注人性当中那些美好的东西,社会无论怎么变迁,道德伦理无论怎么变化,美好的东西都还是存在的,它们不可能是抽象存在么,总是会寄托在某种东西上,无非是社会秩序变化了,它们寄托的对象跟着转移了。放在从前的话,人的道德伦理等等,主要体现在家庭关系上,家庭之外,也更多和他一辈子从事的职业有关系。但现在社会又有新的变化了,过去一个人一辈子也就干一件事情,现在一个人可能不断变换职业,时代发展使得他没法安心于一件事情。譬如一个农民,以前他就面对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他在上面种庄稼,熟能生巧啊,他也了解背后的一整套自然秩序。但这样的情况,即便在凉山有些落后地区都已经非常少了,都几乎消失了。比如,农民在果园里劳动,但那块地已经不属于他了,过去那地上的三棵核桃树,是属于他的,但今天也不属于他了。他只是像在城里打工的工人一样,做一天拿一天工钱,这就是说,原来核桃树代表的那个自然秩序已经不存在了,那他的情感会不会发生变化?如果有了变化,这个变化怎么发生,变化后又是什么样子,原来的情感又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还附着在这块土地上吗?这些都是我要思考的。那么,农村里更多的人,我们也知道都进城和各种机器,还有建筑工地上的瓦块、砖头打交道了。他们的情感应该和过去是不一样的。你要去问他们,他们也说不清楚。但我要是不仅仅观察他们,而是把更大的人群当成对象来观察,就能慢慢感受到一些东西。
傅小平:倒也是。可能作家会比较多关注个别的、局部的现象,但很难把它们切实放到更大的背景下来打量。还有一种情况,要是一味关注国家、政府的层面,又容易脱离具体而微的个体观照,使得自己的感受和观察流于空泛。
阿来:脱贫攻坚,是不脱不行,不攻不行啦。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住上新房子了,可以上的学校质量提高了,也开始看得起病了,国家给农民的福利保障,现在也慢慢有一些了。很多人写脱贫攻坚,着迷的也是这个,而没有具体到更内在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写这方面的文字,但既然这是我在经历的一个大事,我就觉得我应该去经历一下。我也不只是看社会经济发展,我也要看看文明的进步与进化。过去城市发展盘剥农村,工业或别的发展盘剥农业,但在落实脱贫攻坚这个事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有返还机制了,虽然这是政府大力推广在起作用,但中国政府有这么大权力,它完全可以来做这个事情。
傅小平:就写作而言,我觉得关注到这种大的转型背景,还算是基本的。难就难在找到一个切实角度,写出转型时期人们心理和情感的转变。
阿来:对,在这个事上,一方面,我们看到凯歌高奏,但也要看到很多内在的艰难,这些还不是一般工作意义上的艰难。你要有个持续的观察,就会看到这种艰难。我这三年里至少下去走访了二十次吧,但回来也都没写什么文章。认识我的县里的乡里的领导也好,农民也好,老百姓也好,有些是我的读者,他们就说,我们找别人来马上就能看到文章,你来呢,主要就和我们大家交流交流。
贰
所有文本都基于语言,不谈语言只谈其他,那都是扯淡。
傅小平:以我看,你暂时不写文章,是不想写急就章,而是为以后写出更厚重扎实的文章做着长期的准备。就好比汶川地震发生后,你没有马上写相关题材。但十年后,你写出了受到广泛赞誉的《云中记》。也因此,我就联想你写在散文集《大地的语言》扉页上的一句话:我关心的只是,辛勤采撷到的言辞,是永恒的宝石还是转瞬即逝的露珠。其中反映出你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此外要写出好文章,就涉及到怎样运用工具或素材了。做批评想必遵循的是同样的道理。
阿来:所以,接前面的话说下去,有了理论工具以后,就要看你怎么利用这些工具。批评家真正要介入批评,我觉得首先就得贴着文本。如果是在预设的理论框架里分析作品,无论是批评也好,表扬也好,你还是会觉得隔。怎样才会不隔呢,做好两样要贴的东西,就不隔。一是贴语言。你发现没有,现在批评文章几乎不谈语言。语言是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能成立的根本。要是连语言不谈,就谈什么文学形式、作品结构,那都是扯淡。所有的文本都基于语言,要不是通过语言,文学的建筑都不能完成,你怎么能不谈它呢。第二个贴,就是贴对象,你至少得了解一点他为什么这么写,你对他的生活方式,也最好有一点了解。
傅小平:做到这一点了解,没想象得那么容易。有些批评家就说,如果太了解一个作家,反而做不好批评。因为带入过多个人感情因素以后,会影响他的客观判断,而且也会让他下不了狠心讲点真话。当然,这也可能是过虑了。何况,了解一个作家也不是非得跟他做朋友不可,也还是有其他一些途径的。
阿来:所以一个批评家要是什么都不了解,既不贴语言,也不贴对象,他做出来的批评,要我说就算过得去,也还是一个很粗暴的东西。当然,我是在中性的意义上用“粗暴”这个词的。
傅小平:要是我们还没了解一个对象就对其评头论足,至少是缺乏尊重。当然就作品谈作品,要真是进入作品内部,也或多或少能触摸到作家的心灵世界,这种触摸本身,也是你说的“贴对象”的一种表现。问题是,批评家们有时以为自己真正在探讨作品,其实是不得其门而入,只是在作品外围打转。
阿来:很多时候他们以为自己在谈文学,其实是在谈道德原理,他们的很多高头讲章,就来自于道德要求,而不是基于文本。也有时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套用现代派的某些东西,也不是想说这个作家,而是突然发现这一段,能佐证他自己要说的话是对的。
傅小平:这样的情况确实是有的,或许还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批评家们可以反驳啊,我何苦要以作品为中心展开批评,把作品当成为我所用的材料,不是更能体现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
阿来: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完全没有进入到对象内部。苏珊·桑塔格有本书叫《反对阐释》,她反对什么呢,反对的是很多批评家对作品做社会学阐释。她的某些观点我是赞成的。
桑塔格
《反对阐释》
傅小平:做社会学阐释的结果是,很多批评文章都给人感觉有些冷。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冷”理解为冷观察,也可以理解为没温度。你这篇文章虽然用了社会学的方法,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它有激情、有关怀,有思考。透过文章,我也能感觉出你的性情,你的立场。这看似批评应有的品质,但在当下可谓稀缺啊。
阿来:我喜欢的批评家,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对,我也不一定赞同。我就是像读一篇散文那样,读他们的文章,那里面有“我”,有他们自己啊。不像我们很多批评文章,背后是看不到人的,或者这背后的人隐而不见,所以文章读起来也是干巴巴的。说实话,像这种文章我每天都可以写,但写了又有什么用呢。
傅小平:所谓的没“我”,或是“我”隐而不见,也许不只是通过文章看不到“我”的性情,还看不到“我”独立的见解。
阿来:其实不光是文学批评里要有“我”,对客观性要求更高的历史著作里也要有“我”。我为什么喜欢读外国学者,包括汉学家们写的历史书,我就是接受他们的文体,他们的观点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偏颇,我也还是愿意读它。读我们的很多批评文章,里面的观点再公正,再正确,我也不知道你说了什么,我也不想知道你要说什么。
傅小平:你又说了句大实话。现在有些作家如果说想知道批评家要说什么,他们真正在意的也未必是批评本身。再说,作家自己写批评文章也可以写得很好,甚至写得更好。就拿你来说,你大概没写过专门的文学批评文章,不过你的书评、序跋、访谈、演讲等等里面,其实都涉及批评,我会把它们当批评文章来读。但太多读者把文学批评当成一种有一定之规的文体了。
阿来:现在就缺少文体意识。大家都写同样的题材,譬如同样是论唐诗,我为什么不看我们批评家写的,而是读宇文所安写的呢。我们的批评文章大多数就写成那样,所以我直到最近才读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
傅小平:上次和你交流时,你带着这本书么。我还以为你是重读。
阿来:我过去也留意,知道有这个书。但国内作家写的么,想想可能不会好看,就没在意。但那阵子偶尔一翻,就看了那么一篇,觉得好,所以现在都还在读,出门在外带高头讲章读又不合适,我就带着它,累了的时候,读读很好啊。
施蛰存
《唐诗百话》
傅小平:我也读过几篇,施蛰存先生是在他要鉴赏的诗后,附上自己完整的文章,不是古代那种眉批之类的批注或点评,但能从中感觉到古典诗话的特点。
阿来:是啊,他就继承了古典诗话传统么,他也不是做什么系统的论述。这有什么关系呢。施先生受过现代主义文学熏陶,他很可能比我们今天这些批评家们掌握更多西方理论知识,而且掌握得更为系统。你看他的评点,尤其是有些地方牵涉到心理学的东西,就是推测这位诗人写这首诗时,他个人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读到这些地方,你会感觉到里面透露出来一点西化的东西,但他转化得很彻底,我们即使不说他写得完全中国化了,也至少是完全施蛰存化了。即便是西方的理论,他也都是用自己的话重新说出来么。
傅小平:没留意到你读《唐诗百话》之前,我也就知道他是新感觉作家,那还是文学史灌输给我的“记忆”,我不知道他居然也评点唐诗。但我想他写小说的经验,应该对他写这样的文章有帮助。看来他是能把两者融会贯通的。
阿来:有写作经验的人,一般对语言本身会有更深的体悟。而且他评价这个人怎么样,也不会脱开文本说。无论是建构也好,解构也好,他也不给自己限定什么框架。
叁
你的修辞都不是中国的,你怎么传达属于中国人的感受?
傅小平:相比而言,年轻一辈对西方理论的熟悉程度,估计不亚于施蛰存那一代,对古代文论的了解却可能差一截。他们那一代古文功底也普遍很深。你觉得年轻一代是否有可能在语言和思维层面接续古文的精髓,又该如何做到?
阿来:这是可能的。作为作家,不就是靠语言谋生么。很多事说来说去,最后还得回到语言上来说。这个语言,我们很多人习惯说汉语,我是喜欢说中文或华文。反正不管是具象也好,抽象也好,我都是通过这种语言表达经验、思想。从诞生以来,这个语言历史何其漫长,经过多少沉淀,你能说它不优秀吗?那么中文的源头就是文学,就是诗歌,与之相连的散文,在中国传统里,也是包含了诗歌气质的一种体裁。我是一直强调中国诗歌和散文的传统,像《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我觉得没有很多人以为的那么优秀。中文那么优秀,我们掌握西方的东西,但最终必须回到中文的经验上来。你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西方式的,那你写出来的东西还叫中国文学?反正我是读中国人写的批评文章,越来越感觉出种种不对头。我也经常听人说,谁谁谁写的翻译腔,我是觉得你要能真正做到翻译腔,那就好了。怕就怕你写的东西既没有中文的样子,又没翻译腔的样子。
傅小平:那岂不是成了不伦不类的样子?
阿来:对啊,我们看到的,很多都是夹生的东西。说实话,我的知识储备,还有我文章背后的理论是西方的,但我的语感、我的修辞来自中文,我不认为《水浒传》能教给我们什么,相比来说,我更愿意去读古代的史书,更愿意读《二十四史》,从历史书上我也可以学到语言,司马迁不也注重文学的经验?当然,我主要还是读古代的散文、诗歌。至于要增长小说的经验,我们也可以读拉伯雷的《巨人传》,薄伽丘的《十日谈》,读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还有现代主义文学么。我是从西方文学里头获得对小说的认知的,但我们表达还是必须回到中文上来,我们修辞,遣词造句,还有感受世界的方式,都得是中国的。没有言辞,怎么谈感受?你的修辞都不是中国的,你怎么传达属于中国人的感受?要是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更不要说把中西方文化嫁接,或者更进一步是把两者融会贯通了。
傅小平:从修辞角度看,尤其是你说的诗歌、散文,在古代基本上是用文言文写的,那时的书面语与日常生活用语有很大的区别。现在我们写作用的是与日常用语非常接近的白话文。仅只是弥合古今语言表达的落差,就是个挑战了。
阿来:我们现在讲小说口语化,实际上具体到修辞,还是偏书面语。至少我还是坚持用书面语,我会跟口语表达尽量保持距离,要是写文章,也像日常表达那样写,那还写它干嘛,听评书不就好了么!老实说,完全口语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如果我们完全从书面语返回到口语表达,我们这个语言会越来越粗俗。我们留心就会注意到,平常话说得比较好一点,也是受书面语影响多一点的人。既然平常说话,都是融汇一点书面语才会更好,何况我们写文章呢!
傅小平:我们倾向于认为,批评是批评家、批评界的事。但实际上,作家对批评有自己的思考,只是他们很少公开发声罢了。你刚说的很多话都切中要害。在序跋精选集《群山的声音》里,你还写了这么一句:我不是一个力求公正全面却不幸总是沦于偏狭的批评家。虽是自省之语,却也多少透露出你对当下批评的看法。
阿来:不一定有。如果是有批评,我写这句话,也不是特别针对某一个人,而是更多对自己说这个话,因为有些毛病,自己也可能会犯,但应该尽量避免,即使完全避免很难,你总不能光批评别人,对吧?发现别人有这样的问题,你自己也半斤八两,那就不好了。看到批评家的不足,作家是可以用来诫勉自己的嘛。
傅小平:反过来讲,要看到作家的不足,批评家也能诫勉自己就好了。要有这样的胸怀,双方或许会少点意气之争。但从文学界反馈的情况看,即使大家面子上看着和谐,实际上还是缺少信任,也难有共识。所以近些年一直有人在呼吁,作家与批评家之间要多一些良性互动,这样也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批评生态。
阿来:这个呢,我喜欢布鲁姆的一句话,他说:“在迟暮之年,我将文学批评的功能多半看作鉴赏。”他把文学批评,主要看成一种鉴赏活动,这就对了,也就是你一个批评家,把自己当成普通读者一样,而不是摆一个高姿态。你把介入的姿态放低一点,反而可能得到更多,你和作家之间也会更友善。
肆
搞这么多界限、框架干什么?大家不都是写文章的么。
傅小平:你说话很少引经据典,但你分明喜欢引用布鲁姆的话。除他以外,国外作家、批评家的话,你都很少引用,国内的就更不用说了。
阿来:我可能喜欢他那种批评的方式吧。他说话比较直接,西方理论著作里也有很多为理论而理论,你读起来很绕,但与国内很多批评家不同的是,西方那些搞批评的人,绕归绕,但最后好歹会把自己绕清楚,只是你需要耐心读下去。不像国内,你绕也就绕了,但绕到最后,也没绕明白。其实,美国的批评家里面,我也很喜欢桑塔格。虽然她的很多文章不是谈文学,而是谈摄影什么的,但她讲的有些道理,也适用于文学。我最欣赏她的是两点,一是拒绝阐释,二是培养新的感受力。她是针对艺术说的,但文学难道不需要新的感受力吗?我们文学,也和艺术要处理新的材料一样,要处理一些过去文学没有处理过的新的东西,以及没有面对过的新的情感变化。譬如一头牛、一座教堂、一棵老树,像这些东西,我们过去文学就处理过,已经有沉淀了。但当你面对一个火车头,或是别的什么机器,你就需要发挥新的感受力,因为有些情感因子,是我们过去没有的。
布鲁姆
《西方正典》
傅小平:说得是。对于文学批评,我们比较多强调理解力,其实感受力很重要啊。没有感受,何来理解?像布鲁姆和桑塔格,自然是感受力很强,而且很精确的,所以时时有自己的创见。你觉得国内有这样的大批评家吗?
阿来: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我期待。
傅小平:其实批评有没有创见,首先得看有没有谈真问题,要是我们谈论的问题,只是建立在虚假的前提上,或者说出发点就不是那么落实,所谓创见也就很可疑。我记得和你谈《瞻对》时,你说的那句:“史诗是中国人的一个病”,着实对我有触动。我们很多作家有写史诗的心结,但就谈史诗而谈史诗没什么意义。你紧接着讲,我们写作缺的是阐述的能力、表达的能力,以及那种写出情感深度的能力,我觉得才是说到根本了。所以,怎样让批评触及根本,也是个问题。
阿来:还是要把几个东西打通,很多问题用佛教的话说是分别心太多,我们分了文学界、理论界,文学界里面又有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诗人里面还要看你是写散文诗,还是写自由诗。你说搞这么多界限干什么?我们古代没那么条条框框,大家都是写字的么,叫一个写文章的就得了。在我心里,更多就一个文章的概念,其他什么都是可以打通的,各自把各自区隔起来,在比较狭窄的领域里干各自的那摊子事,算什么名堂呢。像苏东坡写文章,他哪会去想到这篇是批评,那篇是什么,他什么都不想,反倒什么都能写好。我现在集中读他的策论,就是他议论国家大事的文章,不也写得挺好,他也写小品文,讨论绘画什么的,也写得挺好。他也是批评家吧!本来么,我们对写文章这个事分门别类,是为了讨论的方便,结果呢,现在很多时候相互之间搞学术纷争、派系纷争了。我们自己画地为牢,自以为写散文像散文,写批评像批评,其实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了。
稿件编辑:傅小平 新媒体编辑:何晶







 窥视卡
窥视卡 雷达卡
雷达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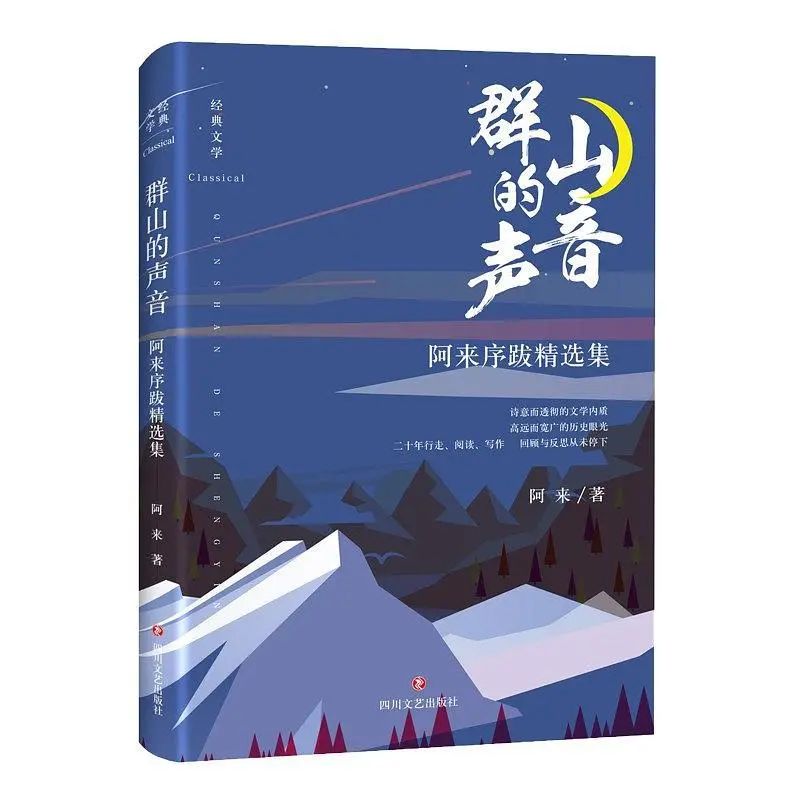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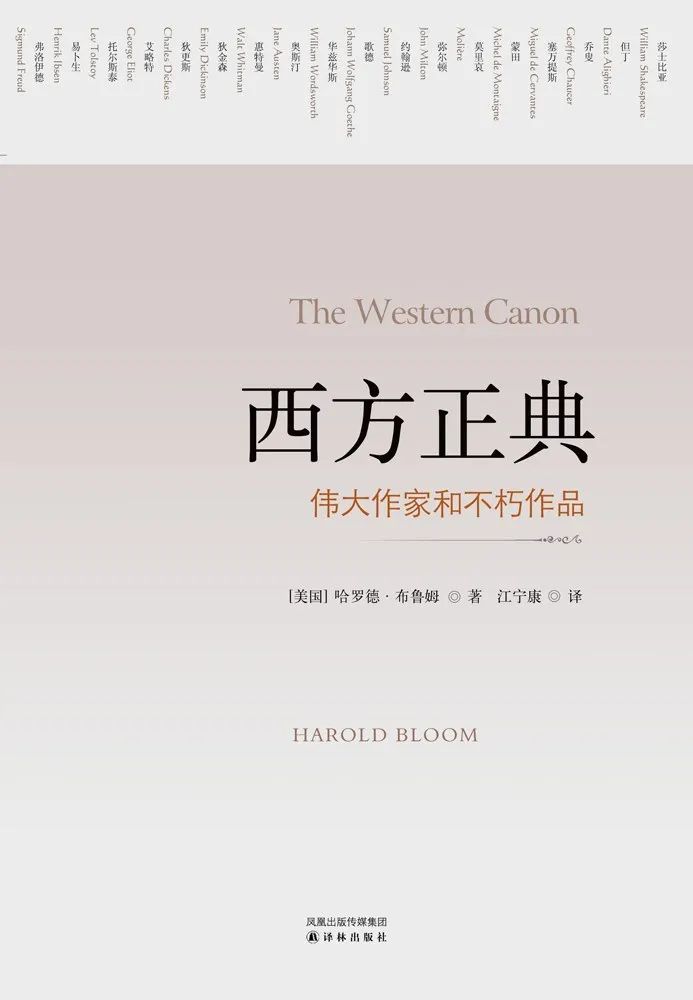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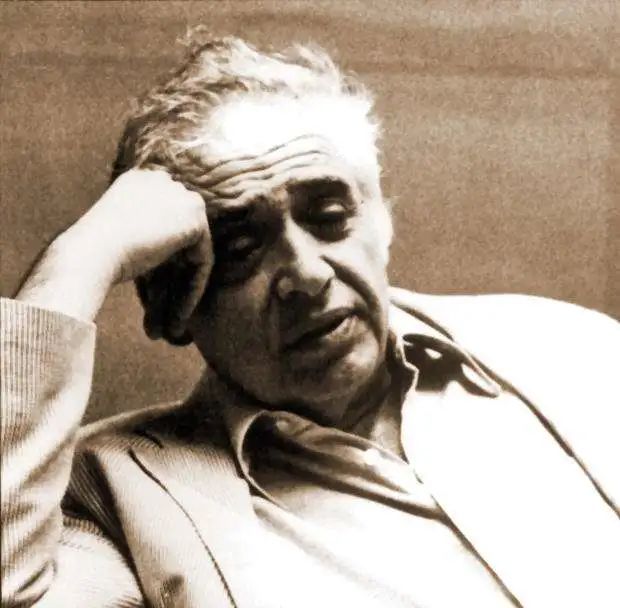
 提升卡
提升卡 置顶卡
置顶卡 沉默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变色卡 千斤顶
千斤顶 显身卡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