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风流!夏坚勇万字散文《诗言志》写活了大扬州!绿杨风2018-10-04 07:04:04
最近,著名作家夏坚勇先生考察游历扬州之后,认真构思,精心伏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写出一万二千字的《诗言志》,文中将历史与现实、文化与市井糅为一体,思路开阔,笔力雄厚。 政经君今天隆重地全文推送这篇精美的大文化散文,供大家品读。同时,政经君还特地邀请另一位大文化散文名家、江苏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吴光辉先生进行精彩评析。吴光辉先生的《诗言一座城市之志——读夏坚勇先生的〈诗言志〉漫笔》同样文采斐然,令人回味。 
诗 言 志 夏坚勇 诗言志,歌咏言。——《尚书·尧典》 我的老家在海安西南乡,历史上属于扬州府,虽然距离扬州将近二百里,但文化风习七不离八,作为地域文化密码的方言也大抵是相通的。老家的方言中,有时一句简单的话要加进几个衬词,演绎得很饱满。例如称赞某种事物很好的“刮刮叫”,常被说成“刮刮老的叫”;再如对某种事物感到惊讶时的“乖乖”,常被说成“乖乖隆地咚”。扬州人也是这样说的,但他们演绎得更华彩,在“刮刮老的叫”后面,有时还要加上一句:“扬州城里找不到”;而在“乖乖隆地咚”后面,也要渲染一句“韭菜炒大葱”。不仅风趣、夸张,而且押韵,像做打油诗似的,让人不能不叹服:扬州人一出口就是诗。 但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在一个闭塞的乡村里,少年时代的我并不知道扬州人一出口就是“炒大葱”之类的诗。我对扬州最初的印象,来源于家乡的一句俗语:“半夜打㧏上扬州”。这个“㧏”读作gǎng,“打㧏”就是某桩事情只在嘴上说,并不付诸行动,和书面语中的“扬言”差不多。“半夜打㧏上扬州”,其实后面还有半句:“天亮了还睡在床上”,这是点题的意思,就像歇后语那个后缀的谜底,可说可不说。 但为什么是上扬州,而不是泰州、通州或别的什么地方呢?俗语中的有些说法是无法追根究底的,一定要追究,只能说在乡民们极其有限的见识里,扬州是最值得向往的大都市,那里有谢馥春的鸭蛋香粉和三和四美酱菜,有王少堂的《武松》和《皮五辣子》,有早上的“皮包水”和下午的“水包皮”。但所有这些,乡民们是无缘消受的,对于他们来说,扬州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上扬州,只能“半夜打㧏”而已。 
关于扬州更具象化的感受,来自后来中学语文课本上的一首唐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只要这两句就够了,这不仅因为李白的名气太大,更因为其中的“烟花三月”实在太好了,简直好得莫名其妙——你很难说得清它到底好在哪里,只觉得那种灿烂而明媚的春景有如梦幻一般撩拨着你,让你不由得春心荡漾,蠢蠢欲动。这就是诗人所谓的妙手偶得吧。 李白是到过扬州的,而且不至一次,其中开元十三年第一次南游,在扬州几乎待了一年。一年中据说散金三十万,但大概因为过于沉迷于扬州的风花雪月,却不曾留下什么好诗。他欠扬州一首好诗。这次在黄鹤楼送孟浩然,算是还了扬州的文债。大诗人在“妙手偶得”的背后,其实积淀着对扬州太多的欣赏和眷念,因此,一落笔便是千古名句。 烟花三月的扬州温柔而缠绵,在诗歌中仪态万方地向我们走来。 
诗 1985年年初,我来扬州参加省里的一个创作会议,住在广储门外的扬州宾馆。宾馆刚刚落成,还没有正式营业,其实也就三星吧,但当时已经是扬州最豪华的宾馆了。豪华不豪华且不去说,但位置确实不错,出宾馆大门向西不过百步,就是著名的天宁寺,清代康熙和乾隆南巡,都曾在此驻跸。——“驻跸”其实就是歇脚,但这个词只能用于帝王,因为“跸”的本意是车驾,当年的天宁寺,那种扈从如云,翠华摇摇的排场可以想见。 大致也就在这两个皇帝南巡的间歇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担任两淮巡盐御史,曾在天宁寺内设“扬州书局”,主持纂辑《全唐诗》和《佩文韵府》,这两项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工程。但我们去的时候,寺院正在修葺,我们只能从脚手架的空隙里窥测门额上剥落的金粉和前朝帝王的御笔。过护城河向东,就到了梅花岭。 从地理上说,梅花岭的高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它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史上却无异巍巍昆仑,因为这里有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和史公祠。徘徊在那逼仄的回廊里,自然会想到这座城市一再经历的惨痛——不光是明末清初的“扬州十日”,也不光是南宋初年和末年的兵燹。 
以前读过姜䕫的《扬州慢》,记住了小序中的两句:“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名城多难,就如同红颜薄命一样,大凡美的事物总是命途多舛,这似乎是一条定律。面对着这样的定律,谁能不“怆然”而“感慨”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扬州虽然号称中等都市,但总体上还是小城的格局,随便走走,一不小心就到了郊外,姜䕫词中所谓的“荠麦在望”了。城市的色调也说不上亮丽,只有文昌阁向东的三元路有点眉眼鲜活的样子——但毕竟只有一小段。大概我们来得不是时候,干冷。那个冬天又一直没有下雪,缺少了滋润,天地间就显得浑浊。 懒懒的冬阳下,街巷里的行人都裹着臃肿的冬装,那时候已经开始时兴那种后面背着帽子的鸭绒服了,鸭绒服大多是单调的深色,没有什么花头。都说扬州出美女,一提起扬州美女,就会让人想到几个词牌:《念奴娇》、《眼儿媚》、《声声慢》、《如梦令》,还有那个所有词牌中字数最多的:《凤凰台上忆吹箫》。可冬天不是看女人的季节,女人一旦全副“绒”装,既显不出身材,也看不出眉眼,一个个都灰头土脸的。 偶尔有上了几岁年纪的女人穿一件中式的花棉袄,那花色——车前子曾在一篇文章里打过一个绝妙的比方,说是花得古气,“像尘封的扬州漆器”。扬州漆器我见得不多,尘封了是什么样子也没有多少感觉,但崭新的扬州漆画这次倒见识了,就在我们下榻的宾馆里。 
那就回宾馆看漆画去,一边和文友们讨论出典。 那无疑是这家宾馆最华彩的门面,大厅正中,金碧辉煌的一幅漆画,几乎是横空出世。如果不看题图,你说是《瑞鹤图》也可以,说是《欢乐颂》也可以。但题图当然是有的:“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 我和文友们都认为这样的句子一定出自唐诗,而且一定是开元时期的盛唐,不然不会有这样的风神气度,也说不出这样的大话、疯话、牛皮话,那个纵情声色,风流倜傥的盛唐啊!但既然是唐诗,那么到底是谁写的,上下文又有哪些句子,尽管诸公衮衮,却谁也“衮”不出个所以然来。 后来才知道,这两句其实不是诗,更不是唐人的,而是两句熟语,典故出自南朝殷芸的笔记小说,略云: 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 
这个“其一人”真是绝顶聪明,也绝顶贪婪,在他看来,有了权势、财富,甚至得道成仙(骑鹤之谓也),固然都不错,但如果不能到扬州去消受,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他“欲兼三者”。 虽然不是诗,但我却认为,在所有关于扬州的评价中,这两句是最富于诱惑力的。是的,关于扬州,他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坦露了自己贪婪的心愿。但在这心愿的背后,恰恰折射了当时全社会的价值观:不到扬州来,人生就不能算完美。我估计后来的那几位帝王都是受了这厮的影响,因为,要说贪婪,谁还比得过帝王呢? 小说家为扬州留下了两句堪称经典的熟语,诗人却留下了浩浩荡荡的诗行。可以武断地说,以诗的形式把登峰造极的赞美献给一座城市,扬州得到的如果不是最多,也肯定是“之一”。 浩浩荡荡的诗行,摩肩接踵的诗人啊!光是一个唐代,当时在诗坛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多名列其中。 
最有名的当然是李白、杜甫、白居易。写得最多的则是杜牧,他早年曾任牛僧孺淮南节度使幕府,也就是说,别人大多是走马看花的游客,他是常住扬州的,自然要写得更多些,“十年一觉扬州梦”,他赢得的又岂止青楼艳名?这些叱咤诗坛的大牌我们先不去说,只说几个很普通的诗人,因为普通这个词总会让人有一种朴素的亲和感。 其一,杜荀鹤《送蜀客游维扬》: 见说西川景物繁, 维扬景物胜西川。 不仅有赞美,而且还有扬抑,有比较。当然,在这之前,人们已经做过这种比较,结论反映在一句谚语中:“扬一益二”。平心而论,成都(益州)也是好地方啊,天府之国,不论山水人文还是富庶程度都令人向往。中国自古就有“少不入川”的说法,就是因为那里的日子太惬意了、容易玩物丧志。但是与扬州相比,它还是显得“二”了,这没有办法。 其二,徐凝《忆扬州》: 天下三分明月夜, 二分无赖是扬州。 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其中不仅有扬抑,有比较——和天下所有的城市比较——还有量化评判,“二分明月”亦从此成为扬州的典型意象。不要追究他这个三分之二是怎么算出来的,诗人是感情动物,情之所至,一出口往往惊世骇俗。试问,有谁量过李白的“三千丈”白发吗? 其三,张祜《纵游淮南》: 人生只合扬州死, 禅智山光好墓田。 活着时的消受不去说了,连死了也要葬在扬州。说一个地方好,居然以“死”相搏,登峰造极了吧? 这个张祜,就是写出过“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的张承吉,他这次使出“洪荒之力”,似乎有意要向徐凝叫板似的。这也难怪,在此之前,他刚刚在杭州和徐凝因“擅扬之争”引出了一场聚讼纷芸的文坛公案。 
当时白居易在杭州当刺史,徐凝和张祜都去走他的门子,希望得到他的赏识,以杭州第一名的身份赴京应试。要说两人的才情和知名度,原就难分伯仲,白居易这个老娘舅也实在不好当。他只得让两人当场比试诗文,最后评定徐凝胜出。张祜大不服,放歌长啸而去。 后来他客居扬州,偏巧遇上意气相投的杜牧,杜牧赠诗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这是力挺张祜、为他打抱不平的意思。但张祜“到底意难平”,或许他知道徐凝有“二分明月”的诗,便在《纵游淮南》中以“死”相搏,力求出奇制胜。因为是写扬州的诗,两人的这次文场对决,要由扬州人来评定高下了。 扬州人评定的结果仍然是:徐凝胜出。 这样说有根据吗?当然有。 
任何一座城市的地名大全,大抵都是可以作为人物志、风俗志,甚至大事记来读的,因为这些都在地名中留下了丝丝缕缕的印记。手头有一本《扬州城老街巷》,涉及的地名林林总总,凡七百余处,其中与人物有关的也不在少数。光是“总门”,例如巴总门、黄总门、谢总门、余总门、马总门等等,就有十多个吧。“总门”这样的地名标识在别的城市恐怕不多见,它是扬州盐商的遗迹。当年盐商大贾们携家带口落户扬州,以同一姓氏聚族而居,进出于同一个大门,这个大门就称之为“总门”。 可以说,每一座“总门”背后,都有一段玉堂金马富比王侯的历史。除去“总门”,像曹家巷、常府巷、刁字巷、黄家园、蒋家桥、石将军巷、李官人巷之类,也都是与历史上的某个人物有关的。但这些人物在地名上的流风遗韵只有姓氏——有的甚至连姓氏也没有,只有身份,如“太师第巷”、“状元巷”、“探花巷”。——以人物的姓名全称命名的地方,全扬州只有两处,一处是史可法路,一处是徐凝门街。史阁部是扬州的精神坐标,扬州理所当然地应该有一条史可法路。 但徐凝只写了一首《忆扬州》,却为之命名了一座城门(徐凝门)和一条街,这不能不说是扬州人对他的偏爱。偏爱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写出了这座城市美的灵魂——二分明月。对此,心气高傲的张祜只能担待着点了。 那次在扬州的会议结束后,正值省里的戏剧会演开场,我写的一个话剧亦恭逢其盛。该剧由富有话剧传统的南通市话剧团演出,特邀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金牌导演杨宗镜执导。我从扬州直接去南京与剧团会合,见了杨导,我说:“你下一趟江南不容易,会演完了,顺便去扬州看看吧。”他哈哈一笑,用一种夸张的舞台腔调侃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老夫去也!”在那一瞬间,我甚至怀疑他以前导演过京剧。 但“老夫”随即又转换成日常腔调:“你算算,十万贯铜钱该有多重,腰里缠得下吗?这唐诗,多大的气魄!” 他也认为那两句是唐诗。
言 那次离开扬州后,心里便常常想到那里的寻常巷陌和市声人语,有如童年梦境中的某个场景,带着故乡熟悉的气息。那期间,“寻根文学”风头正劲,文坛上的老老少少都在忙着“寻根”,我想我的根应该在扬州吧。后来我写过一篇题为《卷帘格》的小说,算是小中篇,背景就是扬州。
“卷帘格”是灯谜中的一种谜格,与杜牧的《赠别》诗——“卷上珠帘总不如”——没有关系。我想通过几个谜友的故事,写出一点扬州文化特有的味道。灯谜这玩意蛮有意思,“谜”者“迷”也,但多了一个偏旁:言说,也就是用语言设置的迷局。写成小说,可读性应该没有问题。作品中有一则灯谜,谜面是:“张翼德查户口”,打七唐一句。“七唐”就是七言唐诗。 
谜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刘禹锡《乌衣巷》中的句子。结果在谜坛引起了一场争论,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说不好的理由是:张翼德那个时代没有户口制度。这些学术问题我就不展开说了,展开说至少需要三万字——那是我小说的篇幅。还有一则灯谜:“刘邦大笑,刘备大哭”打一字。谜底是:翠。因为“翠”字拆开为“羽卒”,卒就是死。项羽死了,刘邦大笑;关羽死了,刘备大哭。如此而已。
你看,一则小小的灯谜,内里是多大的乾坤,其中有诗书典籍的底蕴,又充满了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无论制作还是猜射灯谜,绝对都是很机巧的事。扬州人就具备这种机巧。自明清以降,繁荣的商品经济和发达的市民社会孕育了这种城市性格。当然,机巧可能走向油滑,也可能走向智慧。前一类的代表是皮五辣子;后一类的代表,古代有郑板桥,现代有朱自清。而他们的总和,就是扬州人。
1999年底,我为了考察大运河,第一站就到了扬州,住在市中心的萃园饭店。进了宾馆大门,我突然想到了那则“刘邦大笑,刘备大哭”的灯谜,且继续往下想:眼前这个“萃”字如果制成灯谜,该用什么谜面呢?“萃”字拆开是“草卒”,用“绿地荒芜”如何?但绿地不光有草,还有树。那么“草坪荒芜”呢?也不行,谜面和谜底都有“草”,相犯,这是不可以的。《现代汉语词典》在解释“灯谜”时举例:“齿在口外”,射“呀”字。谜面和谜底中的“口”就相犯了,这很不应该。我说的是商务印书馆1983年的版本,不知后来改了没有。 
萃园饭店门前就是三元路,不过现在改名文昌路了。改名后的文昌路,收编了三元路两头的琼花路和石塔路,成为贯穿城市东西方向的通衢大道。“收编”这个词有一点拿大,但文昌路有资格拿大,因为它的名字好,最富于扬州特色,众望所归。文昌路因文昌阁而得名,旧时代的扬州人,但凡结婚娶亲,不管男女双方家住何处,哪怕近在咫尺,花轿也总要到文昌阁转一圈,为新人讨个吉利。
对于这一点,我深为叹服,扬州城里有那么多寓示吉祥如意的好地方,福禄寿喜财各有主宰,为什么单单要到文昌阁来呢?说明扬州人还是最崇尚文化,这是一座城市光荣与梦想的底蕴。
扬州最不缺的是历史和文化,而且这历史和文化不光是在博物馆里陈列如仪,更是在城市的街坊巷闾间秋波流盼。如果说十几年前的三元路一带还有点粗头乱服,眼下的文昌路已经说得上风姿绰约了。“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我在好几个城市都看到过这样的宣传语,其中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标榜。但扬州的文昌路却一点也不是标榜,甚至还是收着说的。
例如,都说古运河边的琼花观与那个风流皇帝杨广下江南有关,其实它更早的历史应该追溯到西汉年间。那么就不管它唐宋还是汉唐,且一路闲逛吧。边走边看,不经意间就翻动了一页史书。那个夸夸其谈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竟然在扬州做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官,不知他有没有入乡随俗,学得几句扬州话;也不知他的行政能力能否称得上“老马”识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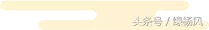
清代的两淮盐税在中央财政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而掌管两淮盐政的衙门,就在这座现在看来并不很堂皇的院落里。当然,最让人感慨万端的还是木兰院寺壁的那首《碧纱笼》诗,“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道出了多少世态炎凉的人生况味。毕竟,俗世红尘,谁不曾遭遇过势利眼呢?
文昌路向东到了解放桥,就是古运河了。这里是真正的唐宋运河,当年,满载着大米、丝绸和各种方物土仪的漕船就是从这里连袂北去的。那是怎样一脉富足、通达而又懂得解读风情的生命之水啊!它的两岸流动着升平年代的人间烟火,引车卖浆也罢,画船箫鼓也罢,全都是一派活泼泼的真性情,洋溢着农业文明特有的古意和温馨。
大运河让北国和江南,荒漠和大海,西域和东瀛,太平洋和印度洋甚至地中海挽起手来,共同演绎着跨越东西方文明的灿烂篇章。在差不多穿越半个地球的漫漫长途上,驼铃清脆,帆影连云,弦歌嘈杂,灯红酒绿,那是怎样一种令人神往的盛世风华。而地处长江和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则成了华夷杂处的国际大都市。“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 
扬州的繁华让杜甫这样的古板人也潇洒起来,你看他说得何其轻巧,似乎只是为了打听淮南的米价,他一滑脚就下了扬州。那么,为什么打听米价要到淮南来呢?恐怕不仅因为这一带盛产稻米,更因为当时扬州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就像现在要了解黄金价格走势要问华尔街一样。
据复旦大学历史系钱文忠教授考证,唐代扬州的经济总量竟然达到全世界的4%-5%。这相当惊人,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能达到这个水平,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在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里,财富增长的速度十分有限,即使所谓的暴富,也只能达到算术级数。而扬州的经济形态属于异类,受惠于大运河的恩泽,这里成为“一带一路”连接线上的贸易热点。
商业活动——买进卖出,翻云覆雨——几乎就是一种财富的游戏,它使财富的增速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从算术级数到几何级数的跨越。这是真正的暴富,也是支撑钱教授那个百分比的经济学原理。扬州方言中至今还保留着“波斯献宝”之类的说法,“波斯”就不用解释了,指的是西域的珠宝商人。当年他们穿过中亚的茫茫荒漠和祁连山麓的河西走廊来到长安,然后又沿大运河来到扬州。 “波斯献宝”有拿着一样东西到处炫耀显摆的意思。这些都是商人的职业智慧。感谢扬州话中的这些俗语,为我们留下了当年那个国际大都市涉外商贸活动的吉光片羽,它比史书上的记载更加富于温度和质感,也更加富有一个时代的风俗画价值。
1999年年底那个时候,到处都在谈论新千年和新世纪,媒体上推波助澜的回顾和展望,让人们莫名其妙地有一种虚荣心和使命感,似乎那两个“新”都是属于自己的,进入了那两个“新”一切就会万象更“新”。后来才知道,其实新千年和新世纪应该从2001年开始,大家都太性急了。
我不是个性急的人,一般只会想着当下的苟且,不大去想什么诗和远方。在扬州期间,陪同我考察的当地作家老高也不是个性急的人,大概他认为自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了,悠悠万事,都犯不着太急。他早年生过一种类似于进行性肌肉萎缩的怪病,据说是不治之症。他命大,竟活下来了,而且成了一位很不错的作家。但走路时身体有点斜,两个肩膀一高一低,有点像民兵训练中接近敌方阵地时的侧身前进。在那几天里,我跟着“侧身前进”的老高走过好些地方:古邗沟、茱萸湾、御码头、小秦淮河。 
扬州的很多地名都有一股古雅气息,上述的几个或朴素,或清新,或堂皇,或香艳,都是古运河的流风遗韵,其中既有风云际会的大情节,也有风花雪月的小悲欢。回味着千百年前的沧桑旧事,眼前身后则是现实世界的衣香人影,有时禁不住会生出今昔何昔,此城何城的梦幻感。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讨论扬州方言中的俗语,从中窥测一个城市从繁华到衰落的斑斑锈迹,还有某种地域文化性格的时代因由。
扬州繁华的最后一次高峰是在清代前期,当时世界上5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10个,6个在中国: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其中所谓的运河城市就占了4个。在那个时候,天津还以被誉为“小扬州”而沾沾自喜,而后来不可一世的上海却连“小”的资格也没有。可见,扬州不仅牛气,而且哄哄。 但到了清代晚期,随着大运河风光不再,扬州也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秋风惆怅,美人迟暮,一座曾在中国城市史上勃发出经济和文化原创力的扬州渐行渐远。但原先是阔绰惯了的,一旦陷入窘境,架子却放不下来。一方面要虚张声势、假装浮华,摆排场,耍气派,打肿脸充胖子。一方面对外面世界的光怪陆离感到惊恐,便处处装腔作势,大惊小怪,小聪明,玩噱头,却自以为得计。 
如此种种,都是无可奈何的失落感投射在城市性格上的阴影。反映在俗语上,则有“虚子”、“洋盘”、“小刁”等说法。朱自清曾坦率地说:“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朱本身就是扬州人,他总结出的一个“小”,一个“虚”,真是太精当了。毋庸讳言,这些都是扬州人对繁华往昔的挽歌。
当然,城市性格的丰富性在俗语中的折射也同样是斑斓多彩的,扬州方言中也有色调完全不同的另一类词。例如把这个“刮”作为词根,就有:辣刮,厉害;“刷刮”,做事快,利索;“能刮刮”,很能干,虽然稍有炫耀之义。我很荣幸,因为这些说法在我的老家也都耳熟能详。
至于“刮刮叫”,那就更不用说了,扬州人对这个词还有更为夸张的演绎:“刮刮老的叫,扬州城里找不到。”这个“刮”,实在、明亮、活泼,洋溢着蓬勃向上的进取气息,在方言中,恰好与“虚”互为反义。 那天晚上,窗外飘着若有若无的雪花,我和老高喝了一点酒,坐在房间里闲聊,他突然问我:“你知道扬州最早的名字叫什么?” 
我当然知道,扬州就是扬州,禹贡九州,扬州为九州之一。 “错也!”老高好为人师,他也有这个资本。他认为,上古时代的那个扬州过于大而化之了,向南甚至包括广东的一部分。作为一座城市,扬州最初始于吴王夫差。对于这段历史,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只用了三个字:“吴城邗”。那时候“邗”和“干”是相通的,因此,扬州最早的名字应该是这个最富于力量感的——干。
他说得六角铮铮,一边用手指在空中横平竖直地比划着,眼镜后面闪烁着得意的微光。
这个“干”倒是不错,扬州人的那些负面性格、无论是“虚子”、“洋盘”还是“小刁”,其精神底色中都是缺少了这一点——实干。而如果有谁想设计一张新扬州的通行证,也只需要写上这两个字就够了。 志 老高叫高汉铭,典型的扬州人,其作品所取也多是典型的扬州题材,他写过“三把刀”,也写过茶馆和澡堂。那次在扬州,我还借了他一本书,后来一直不曾有机会还。几年前在省作协开会,才听说他过世了。如今,他的那本书还立在我的书架上,每次看到,心里总一阵黯然,眼前也总会浮现出他比划那个“干”字时得意的神态。
其实那个与“邗”字通用的“干”是涯岸的意思,指长江北岸的这片土地,它与“实干”没有关系。实干的“干”当时应写作“幹”。但这种文字学上的考证并不影响今天的扬州人对“干”字的热情,这种追求与时俱进的新生活的热情,有如少女之情窦初开,义无反顾。不错,扬州确实是一座适合生活的城市,这里有个园、何园、瘦西湖的停靠和休憩,有“水包皮”和“皮包水”的闲适和自在,有被“三把刀”调理修饰得很舒坦的时光。 
云淡风轻,日月静好,这些都是很精致的生活。但精致不是生活的全部,更不能沉溺其中。扬州籍剧作家刘鹏春在大型扬剧《史可法》中有几句唱词:“皮包水,包得肚囊都是油;水包皮,泡出一身软骨头。”虽是出自劝降者史可成(史可法堂弟)之口,却不能不令人警醒。
今年七月中旬,踏着兵临城下的热浪,我带着小孙子来扬州旅游。早些年我教孙子背古典诗词,小家伙总不上心,他曾自作主张地把“单于夜遁逃”背成“鲈鱼夜遁逃”,也曾把杜牧的名句背成“玉人无数教吹箫”。现在利用暑假把他带来,让他顺便看看“无数”玉人吹箫的地方。
迎接我的是浩浩荡荡的扬州。 搬出“浩浩荡荡”这样的大词,不光是说人多车多——这并不稀奇,现在连一个二等县城也有车水马龙的壮观——也不光是说城市体魄阔大,了无际涯,城市变化令人目不暇接。还有无需深呼吸就能感受到的蓬勃的生气,眼界所及,有一种风起云涌的大气象。 
风,起于七河八岛。 七河八岛近年来成了扬州的一个热词。在汉语中,这种“七…八…”结构的词组很常见,其中的“七”和“八”都是虚指,形容多和乱的意思。但“七河八岛”却是实打实的,七条河、八个岛,各有芳名。从那些名字中,你不仅能感受到某种文化趣味,还可以大致推断出它们的前世今生。例如那富于农业文明气息的芒稻河、太平岛;具有原始生态色彩的自在岛、聚凤岛;还有和一只传说中的镇河壁虎有关的壁虎岛和壁虎河。
这里是扬州老城区和江都区的连接地带,田畴广袤,阡陌纵横,河汊、湿滩、林带、苇海点缀其间,总面积81平方公里。现在,一座融旅游休闲、科技创新、高端产业和高档社区于一体的生态新城正在悄然崛起。81平方公里,这已经差不多是一个中等城市的体量了,但扬州人在这里追求的不是摊大饼式的简单扩张,而是城市品格的升华。这里不仅是江广一体的大扬州格局的地理中心,而且承载着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的开放气度和理想主义情怀。
登上被称为“扬州眼”的万福桥桥塔,七河八岛尽收眼底,一应功能片区有如天才画师挥洒在宣纸上的墨迹,正在浓淡相宜地向四处漫漶、洇润。朝远处看,作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输水通道的大运河一如既往地雍容浩阔,呈现出流畅的叙事风格。 
它已经流过了数千年的神话和传奇,哲学和史诗,也流过了扬州风华绝代的骄傲和有如凤凰涅槃般的一次次劫后再生,现在,它将见识这座城市在一个崭新时代里史无前例的腾飞。而就在大运河身边不远的地方,仿佛着意要形成一种历史的对应,隐现着扬州高铁站的空间轮廓。运河和高铁,古老和现代,温柔和犷猂,在这个暂时被称作七河八岛的地方脉脉含情地牵手……
扬州的朋友一再说,你如果早来几个月就好了,那时候,正值一年一度的“烟花三月”节,扬州那才真叫仪态万方呢。其实,喜欢一座城市,又何须赶在她节庆的时候去凑热闹呢?就正如知心好友之间,并不会在乎交往中的仪式感,倒往往是素面朝天地不期而至,然后随粥便饭,甚至抵足而眠。但话虽这么说,听了朋友神采飞扬的介绍,我还是对那个时间节点上的扬州充满了好奇。
“一个月属于一座城, 世界上只有扬州”, 你听, 这是怎样的气魄和胸怀。
在那个醉人的三月里,扬州人把他们天性中的聪明发挥到了“绝顶”。一句诗办成一个节,天下的客商来了;一座城建成一个园,天下的游客来了;一个园成就一个赛,天下的跑者来了;一个奖怀念一个人,天下的文人来了。谁说扬州人只有小聪明?这里一个个作为定语的“天下”,透射出这座千年古城正在熟练地运用世界语言讲述“扬州故事”,更彰显了一座城市的节庆活动将影响力的半径指向了世界和未来。
稍微解释一下,这里的一个“节”,是“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一个“园”,是新建成的宋夹城体育休闲公园;一个“赛”,是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一个“奖”,是以扬州籍作家朱自清命名的“朱自清散文奖”。一个月里,要演绎多少精彩!大诗人留下的一句千古绝唱,成就了一个城市追梦的创意和复兴的品牌。面朝世界,春暖花开。 
就说说一个“赛”吧——扬州鉴真国际半程马拉松赛,简称“扬马”。 这不是因为马拉松的场面最为壮观。不是。而是因为在所有的体育项目中,马拉松是最需要毅力的运动,我敬佩有毅力的人。因此我也敬佩举办这项赛事的扬州。
举办这样的赛事,决策者自然会有诸多考虑,你说眼光也好,胸怀也好,甚至说体育精神和城市精神也好,这些都不错。但在我看来,其中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对这座城市,他们有着满满的自信。“扬马”无疑是对城市品质的全方位考量,别的都不说,单说城市形象。央视五套全程航拍直播,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摄像机的镜头对着地面推、拉、摇、移,狂轰滥炸,所向披靡,城市的每一个细部都无处逃遁。 
以前我听过几句顺口溜,说有些城市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怕脏乱差的地方失分,就临时砌堵墙围起来,再刷上几条堂皇的标语。好在砌墙是中国人的传统功夫,从古代的万里长城到现在的麻将桌上,一直“砌”而不舍。那几句顺口溜是这样的:“围墙一拦,标语刷刷,外面好看,里面邋遢”。其中的那个“拦”应读成“皮五辣子”的“辣”,用我老家的方言念起来既押韵又生动。
问题是,你即使把围墙砌成秦始皇那样的规模,能瞒得过空中的航拍吗?但扬州不怕航拍,你所有的推拉摇移、狂轰滥炸、所向披靡,不就是为了把城市的一枝一叶一颦一笑都展示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吗?如此甚好,欢迎展示!同志们辛苦了,扬州感谢你们!
扬州凭什么这么自信?央视直播组导演阐述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解答:“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适合做马拉松,更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可以搞直播和航拍。扬州是有特点和内涵的城市,有东西拍,也可以拍得好看。” 
我想,这里的“有特点和内涵”,如果用于一个女孩子,大概就叫秀外慧中吧。而所谓“有东西”,也不光是指市容和风景,还有历史、文化和整座城市的美学风尚。
扬州园林善于借景。瘦西湖里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借得西湖一角堪夸其瘦。下联是:移来金山半点何惜乎小。当今的扬州人善于借力。借助体育提升城市品质,打响城市品牌,已举办了十多届的“扬马”赢得钵满盆满。
于是有人制成一副对联,上联是:瘦西湖,小金山,半程马拉松。集中了扬州人借景借力的得意之作。有点意思。 可惜下联至今无人能对。 过去有一句话:“人到扬州老。”意思是扬州人物鲜妍,街市繁华,外地人一到那里,就显得乡气、土气、寒碜气。这个“老”是相形见绌的意思,就像前些年流行的那几句说法:到了哪里才知道自己官小,到了哪里才知道自己钱少,到了……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民间语文中的一种修辞手法。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反其意而用之。扬州是如此青春亮丽,活力贲张,正如她的名字一样:“扬”——一个充满了勃勃生机和奕奕神采的动词。《诗经·小雅》中有“载飞载扬”的句子,何等形象!外地人到了这里,自然也会受到激励和感染,潜移默化地变得青春起来,文化起来,自信自强起来——一句话,变得“扬”起来。不信,你来体验一下。
我离开扬州那天正值节令的大暑。车出扬州,天高地广,大运河接天而来,又浩荡北去。极远的地方,拔地而起的“扬州眼”似乎有一种向上攀升的欲望,它在眺望什么呢?空间?时间?还是比空间和时间更为浩阔的精神维度?七月的阳光热烈而慷慨,万物生长,绿肥红瘦,大地一派盛装,仿佛在迎接什么旷世盛典。 
不经意间,我在这段文字中已经把“盛”字用了两次,这说明我可能喜欢这个字,喜欢它的排场和大气,与之结缘的那些词,意思也大多不错。那么,如果用于我刚刚离开的这座城市呢?我想应该是盛开——那种关于美的内容和形式的无所顾忌的生命展示。如今,2500岁的扬州正值青春年华,青春可以堂而皇之地鲜艳亮丽,青春也应该堂而皇之地盛开绽放。想起这几天在扬州的所见所闻,不由得诗心萌动,随口就胡诌了两句:
与其在书斋面壁十年, 不如在扬州闲逛一晚。 反复吟诵,自觉是神来之笔,心中暗暗得意。 可是不对,这句子怎么有点熟?再一想,是山寨了舒婷的《神女峰》。 “神”来之笔,原来如此。
学诗不成,也罢。
回来后东拉西扯写了一篇散记,题为《诗言志》。 那不还是“诗”吗? 写扬州,当然离不开诗。 【作家简介】 夏坚勇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于小说、散文尤其是文化大散文的创作。1989年获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颁发的庄重文文学奖。1996年,文化散文《湮没的辉煌》出版,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并列为当时文化散文的翘楚,该书4次再版,发行10余万册,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首届鲁迅文学奖和江苏省首届紫金山文学奖及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2002年,长篇文化大散文《旷世风华——大运河传》出版,先后荣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2005年,推出长篇历史散文《绍兴十二年》,被誉为“近年来难得一见的长篇历史散文杰作”(吴功正语)。
我知道答案
本帖寻求最佳答案回答被采纳后将获得系统奖励 10 天空金币 , 目前已有 3人回答
| 






 窥视卡
窥视卡 雷达卡
雷达卡
























 提升卡
提升卡 置顶卡
置顶卡 沉默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变色卡 千斤顶
千斤顶 显身卡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