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中如何应对“不匀速的长跑”?格非、刘震云、罗伟章、李洱、石一枫等名家这么说2022-01-30 10:34·中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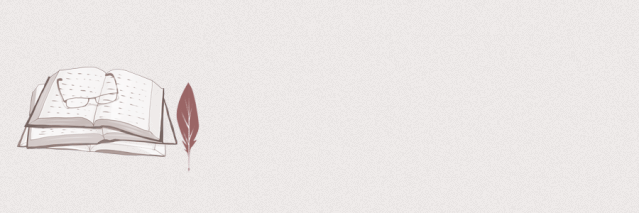  2022年1月24日下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社主办的《当代》2022年度文学论坛暨颁奖典礼成功举办,揭晓并颁发了2021年度长篇小说五佳与《当代》文学拉力赛总冠军。论坛现场,本届长篇五佳得主刘震云、罗伟章与往届获奖作家格非、李洱,围绕长篇创作的甘苦进行了交流,这场高峰对谈以“不匀速的长跑”为题,由《当代》副主编、作家石一枫主持。 石一枫:前面都是评论家在说话,借用钱钟书的说法,假如说作家和作品就是鸡和蛋的关系,评论家在说一些什么话题呢?评论家经常向我们指出这个蛋是白皮蛋好还是红皮蛋好,煎着好吃还是煮着好吃。我觉得这是一个食客的观点,是吃鸡蛋的人的观点。但是在这个环节,我们主要是听一听鸡的意见,让鸡来说一下他们下蛋的甘苦,所以希望几位老师分享一下创作长篇小说的历程。 另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这个题目,“不匀速的长跑”。我们写小说的时候经常拿跑步来做比喻,短篇小说是冲刺跑,是短跑,中篇小说可能是跑两圈就完事,长篇小说通常被我们看成是长跑。如果长篇小说这个长跑是匀速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得有多幸福,你每天都知道自己能够完成一部分工作,你每天都知道明天的方向在哪里。但实际上很遗憾,我们写过小说的人都知道,这个跑步肯定是不匀速的。有的人要跑一年两年,有的人可能要跑七八年,有的人一辈子在跑,有的时候慢,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知道往哪儿跑,有的时候不知道往哪儿跑,有时候摔得大马趴,有的满地打滚,但是我们尽量冲向终点。也请几位老师谈一谈在这个并不匀速的长跑里面的一点体会,谈一谈自己写作的习惯,甚至是自己在某一次写作过程里面经历的事情。  刘震云老师,我刚看过您的《一日三秋》,我觉得跑得很有意思。除了《一句顶一万句之外》,您最近几年好像每部小说都是十几万字,并不是大体量。《一日三秋》也是,看着也非常顺,“奈何奈何”,“咋办咋办”。但是稍微懂一点行的人都知道,这个顺畅的过程里面凝聚着作者的反复考量,可能是每写下一个字的考虑都要比一般人写十个字八个字更多。请刘老师谈一谈您写作时的感受。 刘震云: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文学话题,就是“长篇小说是什么”。当然相对于中篇和短篇来说,你可以说它是长跑;当然可以说它是不匀速的,也可以说它是匀速和不匀速的一个结合。有时候我写完一个长篇,记者会问到一个特别经典的话题,就是你写这个长篇花了多长时间。这个话题对不对呢?它肯定是对的。但世界上只有0.1%是对和错之间的争论,99.9%都是对和对的争论,无非是大对还是小对,是从一公里看是对的还是从十公里看是对的。其实对于作者来讲,真正的写作往往是在不写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不匀速,并不是说你坐在书桌前花了半年时间或者是一年时间,然后把这个作品给写出来的,而是你写之前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来思考这个长篇应该怎么写,我觉得可能对于作者,起码对于我,是更加重要的。 还有一个经典的话题,就是你为什么要写这个长篇,是什么故事触发了你,是什么人物触发了你,是哪一缕炊烟还是鸡鸣让你写长篇?可能对,可能不对,对于我来讲,可能都不是写长篇的起始和初衷。我觉得最大的初衷是顿悟。 我曾经有一个观点:好的作家一定必须是学院派,好的文学背后的底色一定是哲学。 有时候它可能是突然对一个思想和认识的顿悟,这起码对于我写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个认识和思想的基础,接着最重要的是格局,是故事的结构和人物的结构。故事的结构和人物的结构就带来这个小说的节奏,包括它的语言特色。我觉得有时候前面这个比后面要重要,因为我是一个职业的写作者,我看别人的作品,包括中外的作品往往有一种现象,前一本写得还行,到后一本就垮掉了。还有的就是包括这个作者的一生,前两个作品还行,后面的作品就越写越差。为什么?绝对不是因为他不熟悉生活,绝对不是因为生活中没有哪一个人物或者哪一个故事感动了他,是因为他的思想认识在退化,他神经的末梢再长不出来新枝叶。跟生活和其他有关系,但是最主要的关系,在于他对于生活的不断思考。 在休息室我跟格非老师聊天,他就说他给学生讲课,五年一定要把原来讲过的教案重新再抄一遍。为什么呢?因为字看不清了,当然这个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可能五年前、四年前、三年前,你对同一个作品的理解,你信誓旦旦而且用肯定的语言发表的见解,五年之后你突然发现原来是完全错误的。格非老师不断地在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我觉得是一个人进步最主要的原因。 另外,其实我挺喜欢长篇小说这样一种形式,相对来讲比较从容。短篇和中篇有点像奔腾的河流,它对节奏,包括对于意蕴,包括对人物,它要求的节奏是相对,有时候会稍微快速一点。比如河流奔腾而下,突然出现落差就成为瀑布这种景观。这种景观对于长篇小说有作用,但作用非常非常小。我觉得长篇有点像大海,表面的浪花不重要,重要的是海面底下的涡流和潜流,包括它跟太阳、跟月亮、跟潮汐之间的关系。长篇小说非常考察一个作家的胸怀,考察他的认识。有时候我看第一句话就知道这个作家处在什么样的水准,就像乐队的定音。我原来以为乐队的定音是第一提琴手,不是的,那是什么呢?是贝司。 刚才我说感谢评委对《一日三秋》包括我以前一些作品的肯定,这种专业的肯定有时候对作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感觉到了一种温暖;另外,他突然觉得他的创作又自由了一些,可能在下一部作品拓展得稍微宽一点。 石一枫:谢谢刘老师。刘老师前两天有一个视频我也看到了,说文学的底色是哲学,我也认同这个观点。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小说里面提出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永远没有答案的,这个价值是要比说清楚一个问题更重要。下面请格非老师接着说。我看您这些年出版小说非常匀速,两年一个,应该是从“江南三部曲”开始,很匀速地这样下来。您写长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格非:其实一枫你应该自己来聊一聊,你那个新长篇已经快写完了吧,我们都很期待,有机会你也说说你写作的习惯。 至于我,我觉得很简单,刚才震云说的时候我有点走神。为什么走神呢?我在想我这些年,刚才石一枫也说,写长篇为什么两三年写一部?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写作也是不匀速的,所以这个题目我很认同。不匀速的原因不是我不想匀速,我其实很愿意每天像巴尔扎克那样工作,就是早上起来坐在写字台前,或者像叶兆言那样工作,我觉得特别美。但是我在学校有课,而且课程量很大,有半年时间,集中在秋季学期,所以一到八九月份我就开始紧张了。所以写作基本在春节到九月份这几个月当中。到了这个时候觉得时间很宝贵,也增加了很多焦虑感。 写一个长篇,你不可能在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就写完,所以写到一半的时候或者几章的时候就搁在那儿了。过了一年后你重新捡起来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原来写作的那个感情、那种氛围,特别重要的是那个节奏,找不到了,所以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江南三部曲”里面第二部《山河入梦》,写第三章的时候隔了很长时间,那个节奏突然变得很快。有很多朋友,包括莫言也说,你怎么到了第三章突然速度加快了?这个加快就是因为原来的那个匀速的感觉找不到了。所以我到现在还在想这个问题,假如说我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来创作的话,每天都能来延续我的思路,连续不断地把一个长篇写完,这是一个什么感觉?对我来说,已经是差不多二十年没有了。因为一部长篇至少得两年以上才能写完,有的时候一年写一半,有的时候一年写个三分之一。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当然也不是说这种安排没有好处。刚才震云说的我很有体会,好在停一下,因为停一下以后,你会突然发现你原来的想法不一定正确,不一定有价值。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谢上课,人为地让你的思考停下来,要不然的话,你很容易在一种惯性当中来写。所以,当中被人为打断,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有好处。我只能这么自我安慰了。谢谢! 石一枫:以前贾平凹老师说写什么东西,就跑到山里把自己关起来。有时候断一下,像格非老师说的,换一个角度去看,反而感觉会有好处,豁然开朗。但是我觉得这个断也好、不断也好,可能最怕的就是丢电脑。李洱老师,我听说过丢电脑的故事,您来谈一谈吧。  李洱:丢电脑的这个事昨天还有人问我,我就是来人文社的活动吃饭,回家的路上把电脑丢了。《应物兄》没有拷到U盘上,所以电脑丢完之后我一下子就慌张了。后来警察在第三天找到了这台电脑,但是三天时间我头发白了。 刚才两位老师讲得特别好,我的习惯跟他们略有不同。因为我是上班的人,我几乎是打卡上班的人,所以我一直没有整快时间写作,我从来是只要有时间就写,没有说给自己规定这个月写下个月不写,或者早上几点开始写,没有这样。都是上班的时候可以写,在火车上可以写,只要一个人我就随时写。 但是我的难题,相信也是他们两个都可能会遇到的,写长篇最大的难题,就是写作时间很长,你对人物的看法经常出现变化,对人和事的看法会出现变化,跟一两年前不一样,你需要不断地修改。再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的世界观也在变化,你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价值观、世界观。长篇小说肯定写的是对于某种文明的看法,对某种文明状态的看法,对人物关系、对人的理解。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自己原来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出现变化的时候,你就很难把这部长篇小说处理完。你要做的工作主要是修改,不停地修改,以符合你现在的价值观。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作家来讲是个折磨,所以我经常讲这个世界不要变化太快,世界变化慢的话,作者的价值观、世界观比较稳定,会有利于写长篇。我觉得这个时代仿佛不大适合写长篇,但是毕竟还有很多人在写,我也在写。所以我觉得写长篇是一个和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的观念博弈的关系。 后来我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就是把你的价值观演变的过程、你对人物看法变化的过程,也放到小说里面。比如说在具体人物塑造上,让这个人物本身的观念出现变化,通过这种方式似乎可以弥补一下、缓解一下你的写作焦虑。 石一枫:其实像《应物兄》这样的长篇小说的写作方式,在我们现代出版制度之下可能看起来都是奇观。比如说,耗其一生写《红楼梦》这样的事,在古代的环境里面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在现代环境里面,像刚才李洱老师说的,时代的变化包括个人的变化是非常快的,整个出版流程的节奏,有的时候很难容许作家这样去写作。一个小说如果写到十几年的时间,你个人的生活会发生变化。这种在恒变之中不断地调整,确实特别不容易。 李洱:补充两句,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04年,我就是来领《当代》的首届长篇奖,那时我还在做很多很多准备,从活动现场回去的路上还做了一些笔记,把现场的感受带进去。当时我觉得很快就可以写完了,我觉得两年时间肯定能写完。我确实没想到写十三年,这当中肯定会遇到写作中的很多很多困难,有世界观的问题,有价值观的问题,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当然还有个人生活工作的变化,比如说来回调动。但是作家应该克服这些东西,如果不克服,他只要一放下去,就无法捡起来了。这个简直太要命了。比如我这两年还试图在写,但是我只要放下去,想捡起来是太困难了。 石一枫:对,李洱老师小说里面有一段是“从何说起呢”,不知道从何说起了。我跟罗伟章老师上次见面还是在成都喝酒。我想请您从这个具体的场景来聊一下,作家晚上喝酒到很晚,这对每个人好像都是困扰,怎么在头一天喝了酒、熬了夜的状态下第二天还能写作?我想向您请教请教。  罗伟章:其实我的酒量不大,对酒也没有任何的感情。但是确实经常喝,喝了之后就没法写作。比如说我喝醉了一次,肯定三四天是不能写作的,而写出来的也是废的,就是那么一个状况。反正我写作主要是白天写,这跟四川人比较懒散有关系,有一个电影编剧就说你太懒了。我觉得他说得对,因为他们能够克服好多困难,比如说熬夜之后依然可以很有成效地干工作,我不行。如果说觉还差二十分钟没睡,我是不行的,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个觉补足我才可以工作,至少可以满意地工作。所以我是不熬夜的。如果某一次熬夜了,那是我对这个小说太满意了,觉得自己写得太好了,那个地方我停不下来,这个感觉就好。但是这样的时候真的不多。 对我而言,写作非常困难的一点就是这个人物一方面他走向自己,但是另一方面我又需要他走出自己。如果说他没有走出自己,他就不可能真正走向自己。所以在这样一个拉锯当中,我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让他真正走出自己,在这么一个广大的社会整体结构和浩瀚的人生当中去确立他的地位,然后他走回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这是最难的。而且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小说需不需要写、值不值得写的地方,特别是一部长篇小说,篇幅那么长,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我凭什么要写?我经常首先要问,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如果说问不出答案,可能这个就废了。所以我的电脑里面会有好多的半截小说。有一个小说写了二十多万字,那是十年前写的,现在也没弄下去,就觉得没有找到一个路径,在哪个地方撞了南墙,就没找到这个东西。  石一枫:说到喝酒,每次出去别人劝我们喝酒总会说一句话,你们是作家要多喝一点,李白斗酒诗千首,我说你说的那个是诗人,你根本就不懂写小说的。据我所知,好像喝多了酒对写小说一点帮助也没有,对写诗可能有帮助。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作家界有个老大姐,我记得她有一句金玉良言,头天一定睡好觉,如果头天不睡好觉,给你后面的工作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她宁可第一天吃安眠药忍受着上瘾的副作用也要把觉睡足了。其实我们作家写作的时候,都是在适应这种思想的变化、人物的变化、写作习惯的变化、写作环境的变化……种种变化里面可怜地维持着一点恒定不变的写作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小说家确实是挺值得让人心疼的一个行业。当然了,还是钱钟书的那句话,蛋好吃不好吃,我觉得鸡有发言权,但是食客更有发言权。有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蛋自己最有发言权,一个蛋就是一个小宇宙,一个蛋里面包含的信息可能就是我们脑袋里面想出来的一个生命、一段时空、一个世界,然后我们把这个世界奉献给读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挺无私的。所以谢谢大家,今天的对谈就到这里,请大家向写小说的人致一下敬吧! (根据现场发言整理)
来源:《当代》(微信公众号) 编辑:刘雅 二审:王杨 三审:陈涛 
我知道答案
本帖寻求最佳答案回答被采纳后将获得系统奖励 10 天空金币 , 目前已有 4人回答
| 






 窥视卡
窥视卡 雷达卡
雷达卡
_conew1.jpg)


 提升卡
提升卡 置顶卡
置顶卡 沉默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变色卡 千斤顶
千斤顶 显身卡
显身卡
